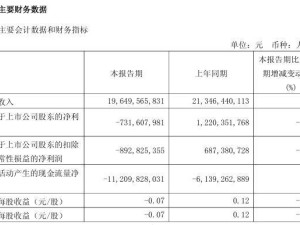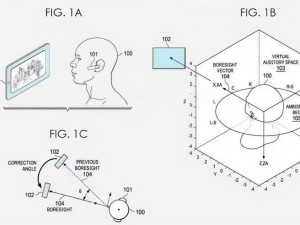记者 刘可欣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引人注目,如果以微观的角度来解读,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从青铜容器这一典型器物来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近日,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带来题为《显著与隐微:阅读三星堆文明》的讲座。他从那些少为人们关注或讨论的知识点,例如三星堆青铜器中隐藏的动态礼仪场景、青铜大立人的三角形“衣领”、青铜器缺失的细节、三星堆与长江文明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以小见大,结合坚实的微观观察,展示了解读三星堆的另一个有趣而独特的视角。
1
从微观角度推测
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或有过木质躯干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数量不少的青铜人头像从来都是博物馆中的焦点。无论是后脑勺编发的,还是头顶盘发的,又或是戴金面具的,它们的下端都呈三角形,且不能独立展示,必须辅以支架。那么三星堆人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不能“站立”的青铜人头像呢?许杰认为,或许是因为人像的有一部分已经消失,只留下青铜的造型。而要解开这个谜题,就需细致地观察青铜大立人。

许杰与青铜大立人,摄于2001年4月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图据受访者)
结合青铜大立人三角形的“衣领”造型,许杰指出,或许这些青铜人头像,都曾有过一个木质的身躯。而这些木质的身躯,已经随着三星堆人的祭祀习惯,如焚烧、掩埋后,消失殆尽。在与三星堆紧密相连的金沙遗址中,就曾出土了木雕彩绘神人头像。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曾与参与一号、二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首任站长陈德安,讨论过这一观点,他们就“铜人头曾有过身躯”这一点达成了一致。这也就引出了讲座的第一点内容:消失的木雕传统。
从这个角度去观察2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也将带来不一样的结果。“2号坑的青铜神坛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木构建筑的青铜模型。”在青铜神坛中上部的青铜人面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相似。而多个青铜纵目面具因有孔洞,不少学者就猜测过,这些面具或是在祭祀场景中,被悬挂于高处使用。因而许杰推测,这个青铜人面像与青铜面具或表现的是同一含义,而其所附依的部分,也许就曾是一个木构建筑。
2
静态的青铜器
是三星堆人独特的“3D”世界
许杰还在现场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这些静态的青铜器中,隐藏了动态的礼仪场景,甚至包含了“场景、声音”,而当时的礼仪活动必然也包含了气味。“研究人员应当从这些有限的遗存中,争取恢复这些场景。”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图源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许杰以二号坑出土的玉璋为例介绍。玉璋上所刻的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许杰认为,这描绘的就是三星堆人祭祀的场景。“两排人都戴着两种不同的‘帽子’。上面站着的一排人带着铜铃形耳环,与耳朵呈90度。而下排跪着的人则带着双环形的耳环,呈45度。”无独有偶,在一号坑出土金杖的纹饰中,人像也带耳环。与玉璋中的纹饰不同的是,金杖人像的耳环呈现自然垂落的状态。因此许杰认为,这些“飞起来”的耳环是制造者的故意为之,它隐藏了人物的动作,表现的是祭祀的动作。
3
纹饰与器型的细微差别
青铜容器与长江中游存在深刻交流
例如从河南安阳殷墟18号墓出土的大口尊与三星堆8号坑出土的大口尊相比,中原大口尊的重心向下,腹部比较深,圈足比较矮,大口相对来说并不高。同时,三星堆的大口尊口部依旧有弦纹,这一点在商晚期的中原青铜器中已经不见。“这是二里岗时期的特征。”许杰说。

青铜大口尊(图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而对于尊、罍来说,中原的兽首放置在容器肩部。而南方的兽首则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跨越肩部和腹部上沿,附着在器物上;另一种则是直接悬挂在器物腹部的上端。这两种形态并不在中原或者南方兼容。
与之相反,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岳阳出土的牺首兽面纹圆尊与商代鱼纹铜罍,与三星堆出土的尊与罍,从器型和兽面装饰上来看,更加相似。并且长江中游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都用于盛放固体,比如玉器和海贝等,而中原出土的青铜容器用于盛放液体,比如祭祀用酒,被称为酒器。许杰强调,同样的器型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会有不一样的使用途径,不应粗略地一概而论。
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与青铜造像之间,无论是从器型、纹饰上来说,均有很大的差别。青铜容器上最常见的饕餮纹,却不见于青铜人像中。“这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大可能存在同一种文化的两个青铜作坊,彼此之前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许杰说,“我认为,这些青铜容器与长江中游存在深刻交流。”
三星堆人对这些青铜容器还进行了一些改造,用于适应自身的需求。比如去掉较高的圈足,或者是在圈足上打孔。或许这些容器也曾有过“顶尊”这样的造型。
象牙、大立人背后的方孔、铜铃、铜挂饰、带彩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器的铸造和设计……现场,许杰感叹于三星堆铸工对视觉、心理的敏锐掌握,同时提醒聆听讲座的考古工作者,对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仔细观察一定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