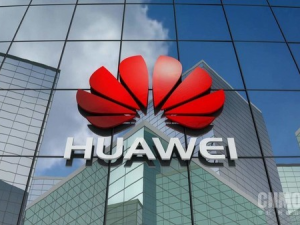今年高考作文题,取材于《红楼梦》中“试才题对额”一回,大观园落成后,宝玉等人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第一处景致:一派好水,一桥一亭翼然水上,贾政欲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
没想到,“沁芳”二字大有来头,在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看来,竟是《红楼梦》全书的总体象征所在。
■ 他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就是“沁芳”
《岁华晴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关于“沁芳”,周汝昌说过: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此名何义?这就应该温习王实甫大师在《西厢记》里给崔莺莺安排的第一个曲子“赏花时”,她唱的是:“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红楼梦》里,众人搬进大观园后,作者正笔详述的第一件事就发生在沁芳闸。
那天正当三月中浣,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即《西厢记》),走到沁芳闸桥那边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从头细看,只见一阵风过,把树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宝玉便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就在此时,宝玉遇见了正要葬花的黛玉,黛玉告诉他:“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
周汝昌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象征全书所写女子的总命运,宝玉是群芳不幸结局的总见证人,因此他题“沁芳”二字必有缘故。而且根据曹雪芹原意,黛玉其实并非因病而死,而系投水自尽;《红楼梦》中曾反复引用“落红成阵”“花落水流红”“流水落花春去也”等诗句;“沁芳”实为“浸芳”,它是沉浸(埋葬)群芳(女子)之水,大观园中的女子在这里相聚,最终却又像缤纷的落花一样,随流水远逝。这就是“沁芳”二字的真正含义。
■ 曹雪芹遗物“天上难寻,人间罕遇”,警惕学术的名利心
周汝昌先生这本《岁华晴影》中,有一篇文章《雪芹遗物》,其意义已然超出“红学”。
此文一开头就是一句“惊人之语”:“做学问最忌的是什么?是名心同利心。名心利心这种东西,常常会化为另一种心——小人之心。”
接下来,周汝昌就以“曹雪芹遗物”为例,讲述了这种小人之心。
如今,曹雪芹的遗物简直是“天上难寻,人间罕遇”。有的红学曹学家,对此梦寐以求,“然而世有黠者,穷极无聊,看出芹迷的心事,遂投所好,钻了空子,炮制出一串假古董,愚弄痴人。于是好事情便被这种坏人搅得一塌糊涂,不明真相,轻易相信的,至今还在对这些骗人的东西津津乐道。”
这还只是“小人之心”的第一层次,然而还有第二层次。
有一位“红友”,笃信骗局伪物,自信是“二百年来的最大发观”,写文章为之宣传,还害怕旁人先知,夺去“发现专利”,直到发表之事统统安排定局,这才对周汝昌“宣布”。周汝昌看后,觉得疑点太多了,不信。可笑的是,对方多次来问:“你的著作里为何不引用我这批珍贵的资料?”周汝昌只好婉言托辞,说:“那是老兄你的发现,我不当掠美。”对方说:“没关系,你还是该引用。”
后来,对方也明白是周汝昌根本不信之故,于是就对人说些闲话,意谓:“周某人竟不相信!要是他发现的,那就不是假的了。”
这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悲又可恨了。
周汝昌自己感喟:“我写文至此,读者阅文至此,似微闻耳际有叹喟之声。”
记者读到此处倒是想起,鲁迅发表《阿Q正传》,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却常被人以为是在影射、攻击某人。鲁迅不由得叹息:“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说来也是有趣,周汝昌先生在书中多处引述鲁迅的意见;而周先生自己,也多次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就是要较真,就是不“雍容大度”。这种态度,实在也有点像他的本家鲁迅。
■ 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壮思堂”有感
《岁华晴影》中,还记述了周汝昌本人一些文字因缘。比如,1979年,周汝昌应邀赴美参加国际红学研究会,认识了那时尚在加拿大工作、居住的诗词学家叶嘉莹。他与叶嘉莹虽不是校友,青年时代却有一位共同的老师——文史学者顾随。更巧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叶嘉莹在北平就读辅仁大学女生部,该部就设在恭王府;而根据周汝昌考证,恭王府就是大观园原型。他将自己写的《恭王府考》一书寄给叶嘉莹,果然引起叶嘉莹对往事的回忆,写来五言律诗三首,“落落大方、情味弥永”,周汝昌读后深受感动。
还有更加奇妙的文字因缘、文化因缘、历史因缘。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周汝昌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日军包围、封锁、解散燕大那一天,他正听系主任谢迪克教授讲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非常精彩入神——而当此际,变生不测了!此事我永难忘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汝昌再度赴美交流,得知谢迪克教授仍健在,已86岁。当初他被日军关在集中营里,还从事《老残游记》的翻译事业。谢迪克教授后来应邀重访北京,他到北大燕园的第一讲,就是重续四十年前被日军打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得知谢迪克教授是《老残游记》的英译者,周汝昌感到兴奋:他非常喜欢和佩服《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是第一个指出,“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就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人,他对《红楼梦》的理解极其深刻。
在美国,周汝昌讲的是红学,感怀的是民族的文化历史。1987年,他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交流,讲《红楼梦》的结构。“进了讲室,已经座无隙地。拾头一看,见讲台上方高悬一匾,写着‘壮思堂’三个大字。我心中着实有所感动——在美国的学府中,却挂着中文汉字的匾额,反而倒不像中国人自己,专门效颦一些‘洋味’,以为不如此不‘高贵’,而不去想一想:我们中华文化在海外是如何地受重视而显辉煌。”
这间“壮思堂”,记者查阅了一些资料,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所在,本名Jones Hall,直译或可译为“约翰楼”。楼里有爱因斯坦办公室,那位患有精神分裂症、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数学天才纳什常在此楼工作,反映他人生的电影《美丽心灵》在这里摄制。这座楼的202室是一个雅致的会议室,正中间挂着中国台湾著名艺术史研究者庄申教授题写的字“壮思堂”,把Jones Hall译作“壮思堂”,真是很妙。